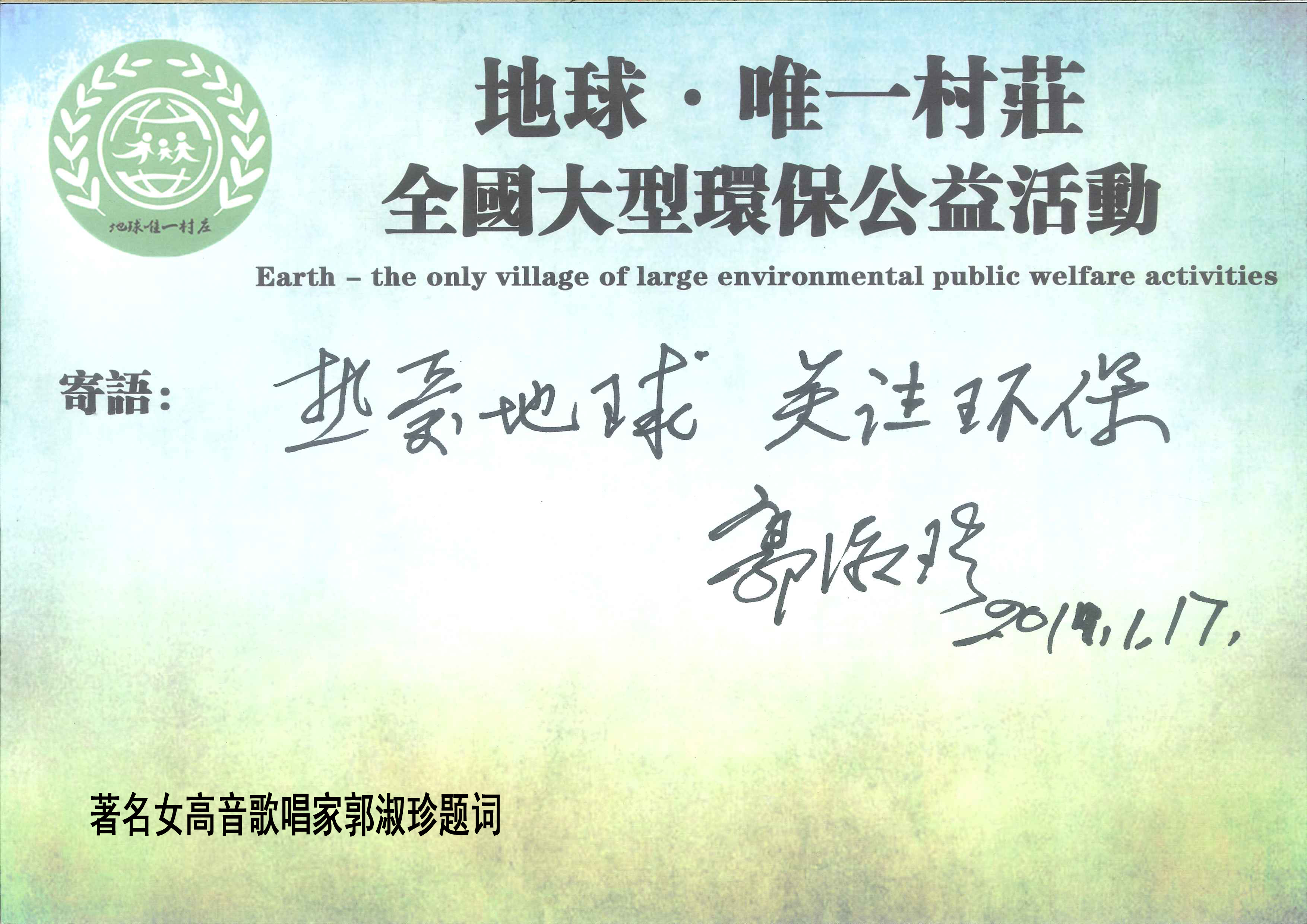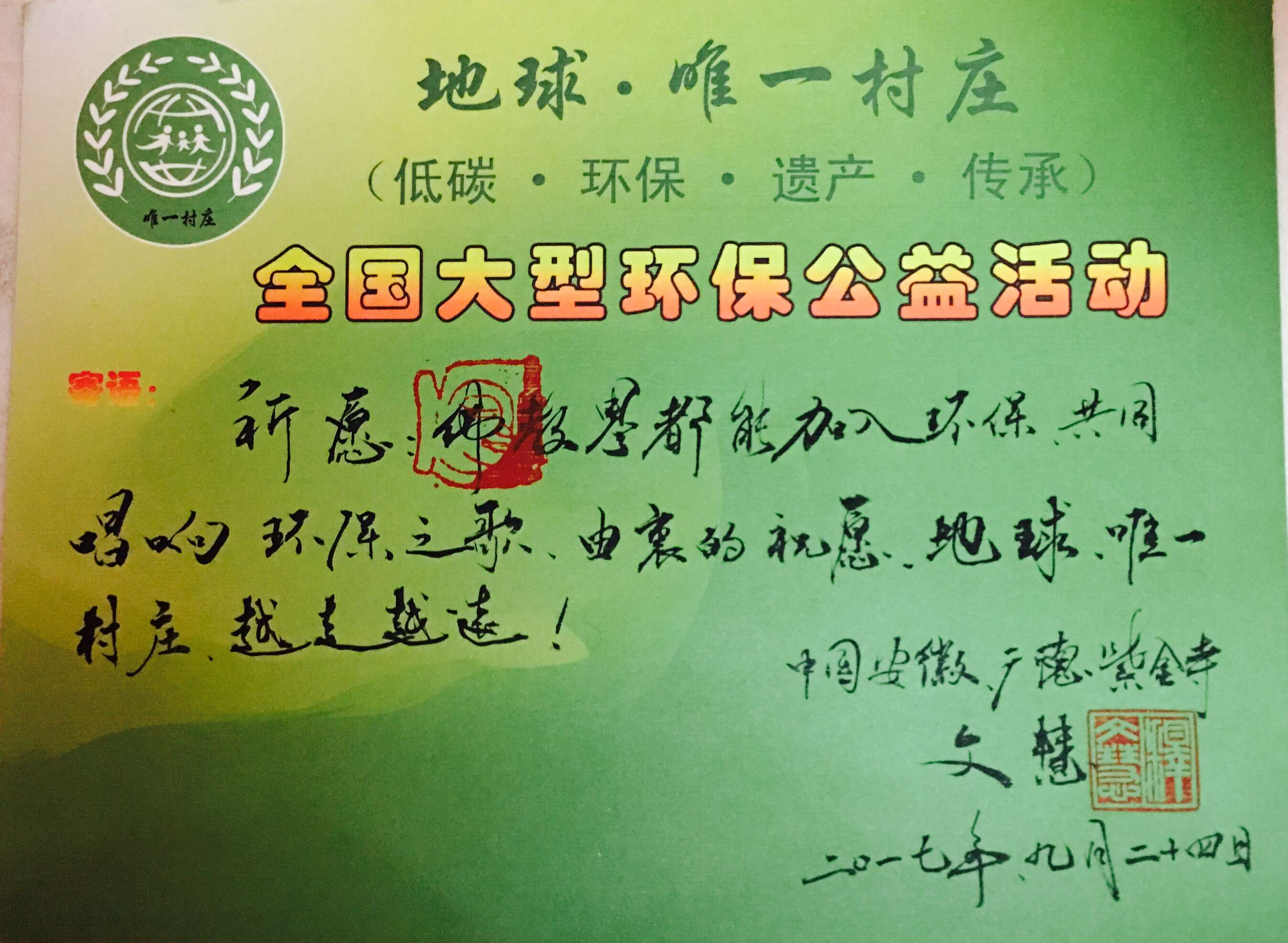麻城市召开“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座谈会
来源:黄冈新视窗网 作者: 时间:2015.04.28
黄冈新视窗网消息(通讯员刘霞 熊瑛 程胜利)4月23日下午,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在麻城市国土资源局六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座谈会。主要参加人员有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及麻城籍将军后代代表。
麻城籍将军后代代表有王树声大将女儿王宇红、王必成中将之子王晓峰、张才千中将之子张亚平,丁先国少将长子丁凯洲、冯仁恩少将之子冯世平将军等出席座谈会并就保护和发掘大别山地区红色文化遗产建言献策。。
大别山区三省党史研究专家学者有湖北省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熊廷华、黄冈市党史办副主任库充、红安县党史办副主任辛向阳,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麻城市党史办副主任曾峰、安徽省六安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马德俊、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蒋二明、霍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祖祥、河南省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姬少华、新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董绍富、原光山县党史办主任袁宗文等研究红色革命史的专家、学者,纷纷为传承大别山红色文化出谋划策。。
研究革命史专家学者有天天在线总裁陈湘安、大别山革命史研究者高晓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宪、安徽大学革命史研究者黄文治、湖北省社科院马克思研究所博士邹荣、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宋其洪、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杰、麻城市民政局老干部史瑞林、麻城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凤梧、麻城市乘马岗镇镇长凌华、麻城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副科长丰红梅、麻城市党史办副主任郑凤珍、麻城市博物馆馆员熊瑛、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熊晖等代表。
座谈会讨论主题为“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与会学者分别就大别山革命史史料收集整理、革命史研究的方法、陈独秀问题、张国焘问题、王明问题及红四方面军相关问题作了讨论。
王宇红首先发言,她强调党史研究要回归人性,要摆脱传统的历史观,大别山苏区史还有很多可以挖掘和研究的角度,很高兴有很多年轻人参加这次座谈会,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她还讲述了王树声的一些战斗事迹,提出要加强对开国将军革命生涯细节与心路历程的挖掘与研究。张亚平认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资料比较少,研究较为薄弱,应该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的抢救与发掘,有些问题现在不能解决,可以集中整理出来留待后人研究。丁凯洲讲到他的父亲丁先国所在的丁家畈99人参加红军,只有家父一人幸存,他们那一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辛向阳说,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上,能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专注红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非常难得。我们红安是将军县,红色革命史资料丰富,凡是将来到红安收集资料并从事革命史研究,我个人会毫无保留地开放。老一代党史工作者对年轻人要多帮助和提携。
熊廷华、马德俊、蒋二明一致强调,鄂豫皖三省革命史研究要整合一体,搭建高层次研究平台。姬少华、库充等充分肯定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并认为此次出版的原生态的《麻城革命歌谣》已经达到相当水准。
黄文治博士从革命史研究方法、革命史史料解读以及革命史研究心得三个层面做了主题发言。首先,就整个中共革命史研究而言,从历史研究法的视角来看,建国后至今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建国以后到文革结束,革命史研究基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宣教;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是实证主义研究;最近这几年解释主义研究学派异军突起。第一阶段属于旧革命史研究,第二、第三阶段属于新革命史研究。相较旧革命史研究而言,新革命史研究重视整体史推演、知人论世及鉴往知来。解释主义学派在重视史料获取、鉴别及还原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注意观念的变动,来达到“深描”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生态、微观行动机制及其探索意义。解释主义学派的新革命史研究,突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结合,重塑观念社会化的过程及手段,并回应、证实、证伪一些先验革命理论、方法及前辈研究成果,注重思想力、解释力的挖掘,最终提出自己的“概念”或者“理论框架”。
有关苏区革命史资料方面,黄博士认为任何历史研究的推展都是以史料的调查与解读为基础的。中共苏区革命史研究,当然需要文献史料的支撑。中国大陆珍藏有关各苏区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联档案及中国台湾“五部档”、“汉口档”、“政治档”等相关档案资料,无疑是革命史“实证”研究的核心材料,但也不能忽视微观资料的整理与使用,比如他几次到大别山革命老区做田野调查,从地方档案馆、党史办、博物馆等地收集到不少包括未刊档案资料、史料汇编、谱牒资料、人物传记、杂忆文集、地方县志、地方文史、革命歌谣、报刊、口述历史等方面资料(尤其是民间史料)。这些资料多且庞杂,但非常有价值。要开展好革命史课题研究,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首要条件是做好史料的编年,其次就要利用好这些主干核心资料及收集到的其它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种基础工作非常重要,比如大别山苏区史上的“商南事变”、“党军矛盾”等问题,不同地方组织、不同参与者,以及不同时期的史料,说法都不一样,这就需要一个“考证”与“考订”的过程,从情境历史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目前有关苏区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档案源开放不够;其二、学者田野调查着力不够;其三、史料编年非常繁琐。
在苏区革命史研究心得方面,黄博士在大别山苏区史研究中发现,大别山区既有穷地方,也有富地方,既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绝对是地富子弟城市串党并积极下乡传播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说地富子弟被他们的父母及家庭长辈送到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及武汉等城市去读书和学习,这些地富子弟在城里读书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组织及新思想,比如中共党组织及其理念。然而1927年前后是个关键的拐点,这些地富子弟因为偶然或者必然因素,将中共组织及理念带回自己的家乡,乡村革命是由回乡革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但是乡村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爆裂性的革命?这又与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整合到了阶级矛盾及阶级仇恨中来,然后进行一个动员。就革命史研究而言,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问题极为重要,两者互为一体。有关1920年到1932年大别山苏区民众动员史过程研究,就必须重视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并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动员其实和土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仇恨和情感驱动的,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暴动。第二阶段是苏区土改的推动,第三阶段重点是苏区反富农的再动员。这其间就有,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互为联动的绩效。很遗憾,在封闭的环境里,这种再动员的一个结果就是走向了“过度动员”。苏区革命即从遇到困境,到克服并适应困境,到最后却制造了更大的两难困境。苏维埃革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所以中共必须长征。这样的话,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三个阶段的轮廓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是“过度动员”,从内部来看,苏维埃革命本身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因此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地步,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因此,中共长征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外部的围剿,更重要的还是中共内部“过度动员”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的。
其他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心得,还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座谈会气氛热烈,最终圆满结束。
麻城籍将军后代代表有王树声大将女儿王宇红、王必成中将之子王晓峰、张才千中将之子张亚平,丁先国少将长子丁凯洲、冯仁恩少将之子冯世平将军等出席座谈会并就保护和发掘大别山地区红色文化遗产建言献策。。
大别山区三省党史研究专家学者有湖北省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熊廷华、黄冈市党史办副主任库充、红安县党史办副主任辛向阳,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麻城市党史办副主任曾峰、安徽省六安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马德俊、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蒋二明、霍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祖祥、河南省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姬少华、新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董绍富、原光山县党史办主任袁宗文等研究红色革命史的专家、学者,纷纷为传承大别山红色文化出谋划策。。
研究革命史专家学者有天天在线总裁陈湘安、大别山革命史研究者高晓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宪、安徽大学革命史研究者黄文治、湖北省社科院马克思研究所博士邹荣、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宋其洪、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杰、麻城市民政局老干部史瑞林、麻城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凤梧、麻城市乘马岗镇镇长凌华、麻城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副科长丰红梅、麻城市党史办副主任郑凤珍、麻城市博物馆馆员熊瑛、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熊晖等代表。
座谈会讨论主题为“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与会学者分别就大别山革命史史料收集整理、革命史研究的方法、陈独秀问题、张国焘问题、王明问题及红四方面军相关问题作了讨论。
王宇红首先发言,她强调党史研究要回归人性,要摆脱传统的历史观,大别山苏区史还有很多可以挖掘和研究的角度,很高兴有很多年轻人参加这次座谈会,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她还讲述了王树声的一些战斗事迹,提出要加强对开国将军革命生涯细节与心路历程的挖掘与研究。张亚平认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资料比较少,研究较为薄弱,应该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的抢救与发掘,有些问题现在不能解决,可以集中整理出来留待后人研究。丁凯洲讲到他的父亲丁先国所在的丁家畈99人参加红军,只有家父一人幸存,他们那一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辛向阳说,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上,能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专注红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非常难得。我们红安是将军县,红色革命史资料丰富,凡是将来到红安收集资料并从事革命史研究,我个人会毫无保留地开放。老一代党史工作者对年轻人要多帮助和提携。
熊廷华、马德俊、蒋二明一致强调,鄂豫皖三省革命史研究要整合一体,搭建高层次研究平台。姬少华、库充等充分肯定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并认为此次出版的原生态的《麻城革命歌谣》已经达到相当水准。
黄文治博士从革命史研究方法、革命史史料解读以及革命史研究心得三个层面做了主题发言。首先,就整个中共革命史研究而言,从历史研究法的视角来看,建国后至今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建国以后到文革结束,革命史研究基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宣教;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是实证主义研究;最近这几年解释主义研究学派异军突起。第一阶段属于旧革命史研究,第二、第三阶段属于新革命史研究。相较旧革命史研究而言,新革命史研究重视整体史推演、知人论世及鉴往知来。解释主义学派在重视史料获取、鉴别及还原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注意观念的变动,来达到“深描”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生态、微观行动机制及其探索意义。解释主义学派的新革命史研究,突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结合,重塑观念社会化的过程及手段,并回应、证实、证伪一些先验革命理论、方法及前辈研究成果,注重思想力、解释力的挖掘,最终提出自己的“概念”或者“理论框架”。
有关苏区革命史资料方面,黄博士认为任何历史研究的推展都是以史料的调查与解读为基础的。中共苏区革命史研究,当然需要文献史料的支撑。中国大陆珍藏有关各苏区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联档案及中国台湾“五部档”、“汉口档”、“政治档”等相关档案资料,无疑是革命史“实证”研究的核心材料,但也不能忽视微观资料的整理与使用,比如他几次到大别山革命老区做田野调查,从地方档案馆、党史办、博物馆等地收集到不少包括未刊档案资料、史料汇编、谱牒资料、人物传记、杂忆文集、地方县志、地方文史、革命歌谣、报刊、口述历史等方面资料(尤其是民间史料)。这些资料多且庞杂,但非常有价值。要开展好革命史课题研究,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首要条件是做好史料的编年,其次就要利用好这些主干核心资料及收集到的其它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种基础工作非常重要,比如大别山苏区史上的“商南事变”、“党军矛盾”等问题,不同地方组织、不同参与者,以及不同时期的史料,说法都不一样,这就需要一个“考证”与“考订”的过程,从情境历史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目前有关苏区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档案源开放不够;其二、学者田野调查着力不够;其三、史料编年非常繁琐。
在苏区革命史研究心得方面,黄博士在大别山苏区史研究中发现,大别山区既有穷地方,也有富地方,既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绝对是地富子弟城市串党并积极下乡传播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说地富子弟被他们的父母及家庭长辈送到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及武汉等城市去读书和学习,这些地富子弟在城里读书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组织及新思想,比如中共党组织及其理念。然而1927年前后是个关键的拐点,这些地富子弟因为偶然或者必然因素,将中共组织及理念带回自己的家乡,乡村革命是由回乡革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但是乡村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爆裂性的革命?这又与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整合到了阶级矛盾及阶级仇恨中来,然后进行一个动员。就革命史研究而言,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问题极为重要,两者互为一体。有关1920年到1932年大别山苏区民众动员史过程研究,就必须重视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并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动员其实和土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仇恨和情感驱动的,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暴动。第二阶段是苏区土改的推动,第三阶段重点是苏区反富农的再动员。这其间就有,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互为联动的绩效。很遗憾,在封闭的环境里,这种再动员的一个结果就是走向了“过度动员”。苏区革命即从遇到困境,到克服并适应困境,到最后却制造了更大的两难困境。苏维埃革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所以中共必须长征。这样的话,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三个阶段的轮廓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是“过度动员”,从内部来看,苏维埃革命本身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因此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地步,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因此,中共长征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外部的围剿,更重要的还是中共内部“过度动员”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的。
其他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心得,还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座谈会气氛热烈,最终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