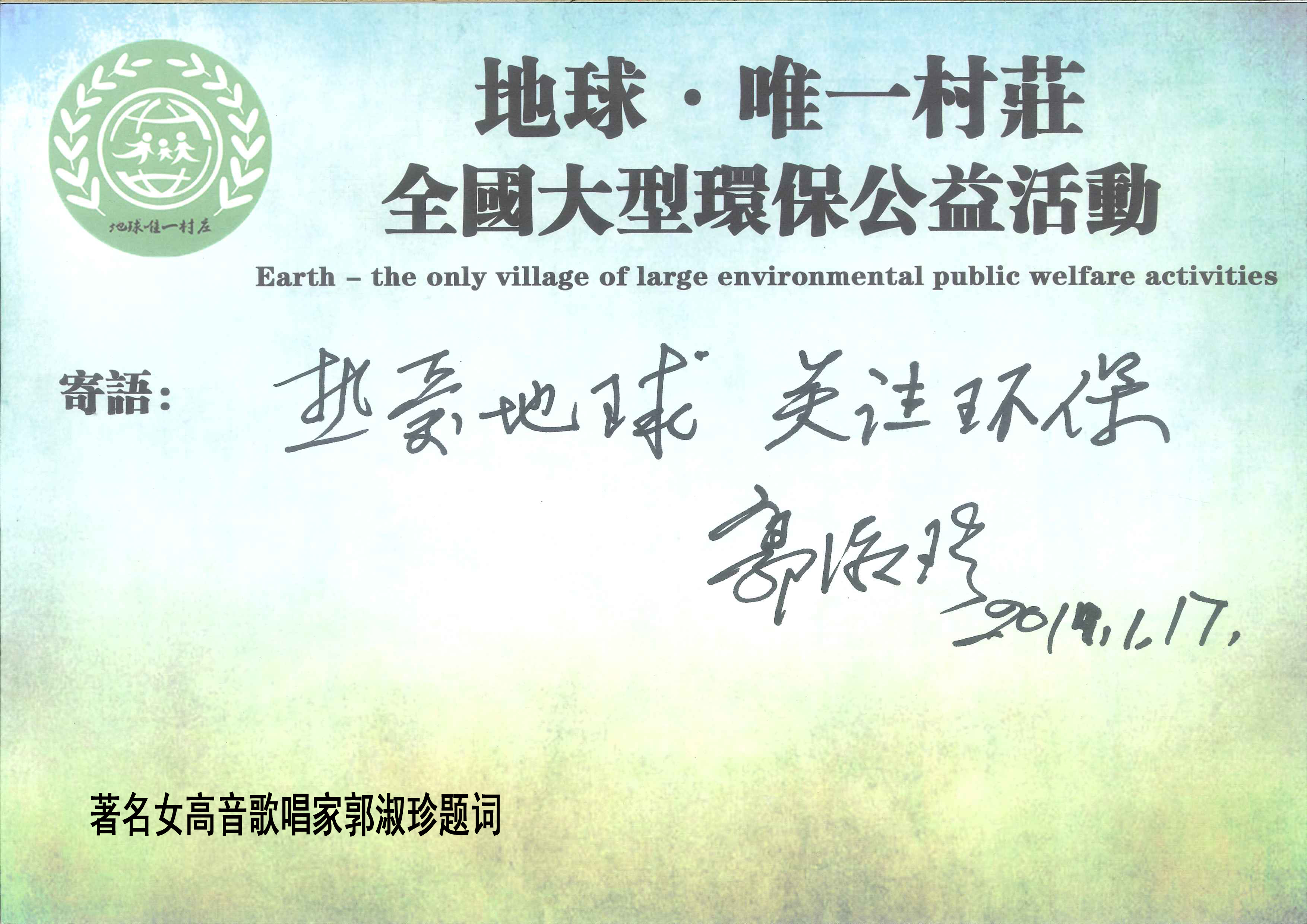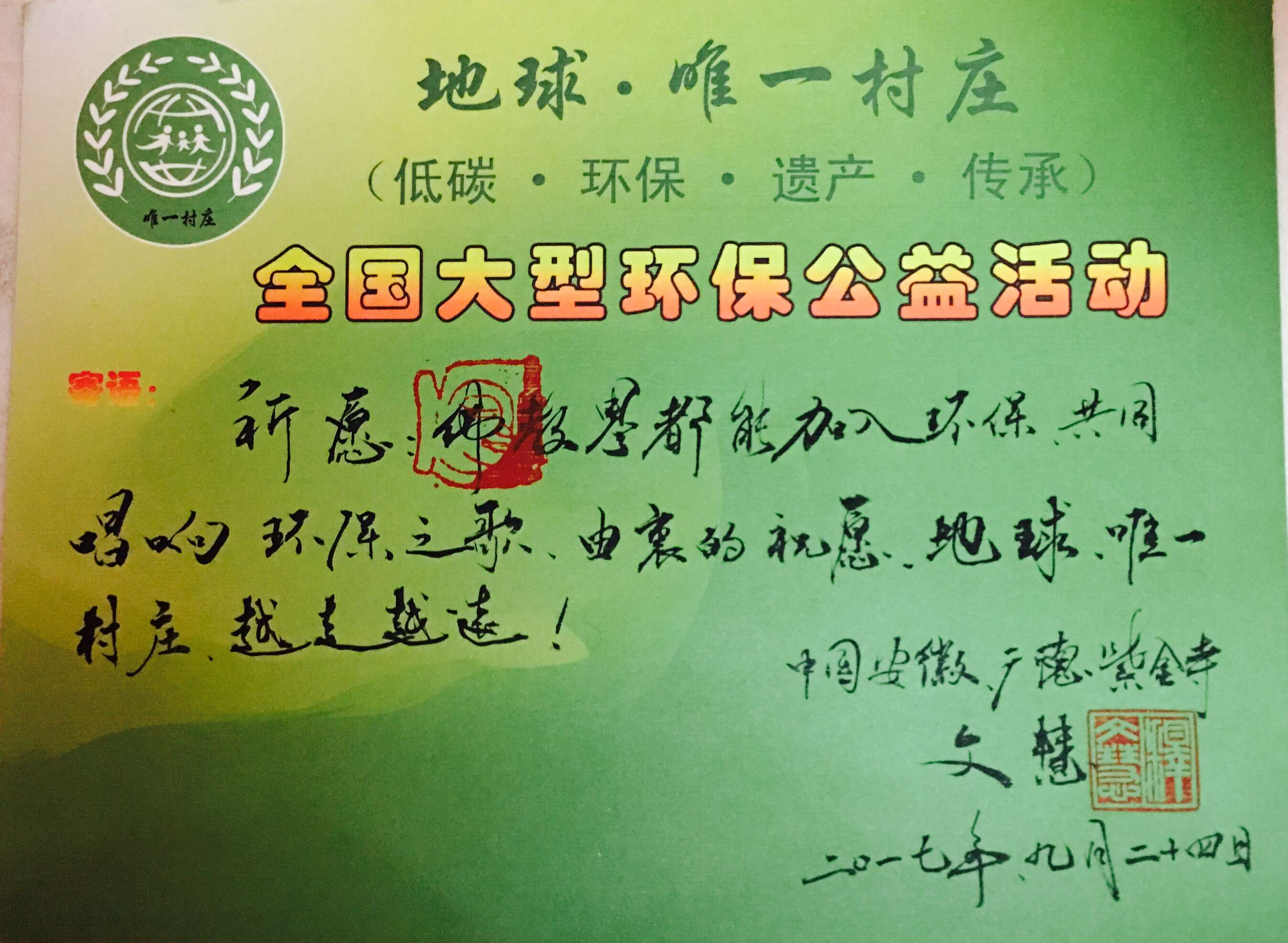非遗产权与传承困境
来源:《瞭望》 作者: 时间:2014.08.08
随着“老字号”品牌商品价值日益凸显,围绕品牌权利继承所引发的争端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市场并不看好的非遗项目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优秀典范。与前些年非遗保护的资金困境相比,在国家各个层面的重视和支持之下,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不差钱”。
但随着“老字号”品牌商品价值日益凸显,围绕品牌权利继承所引发的争端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市场并不看好的非遗项目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专家认为,新时期的非遗传承保护必须跨越这两道坎,才能实现传承的健康有序。
产权背后的利益纠葛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在天津当地,一公一私两个“泥人张”之间却由于商标归属,有着长达20多年的争议。双方在传承理念上存在矛盾,经营上彼此竞争,这也成为“泥人张”传承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
今年36岁的张宇是“泥人张”第六代家族传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官司分散了他很大的精力,其中最让他揪心的是与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官司。
本刊记者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的二审判决书中了解到,1958年天津市政府在市文化局领导建议下,成立了由张明山后代参与的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培养了新一代家族传人及非张氏“泥人张”彩塑艺术传人。随着张家后人从工作室退休,工作室自行将“泥人张”申请注册商标,独立拥有,并与家族传人在市场上竞争。
法院最终判决,彩塑工作室和张明山后代中从事泥人张彩塑创作的均为“泥人张”无形资产共有人,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工作室已注册的“泥人张”商标和“天津泥人张彩塑”服务标记应自行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
在法院判决“泥人张”名称使用权归双方共有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泥人张”家族传人与彩塑工作室各立门户,互相竞争。工作室所持有的商标也未申请撤销。第四代家族传人张铭的后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水火不相容。
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主任傅长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其设立和培养学生的主要宗旨是挖掘和推广泥人张彩塑艺术。他也坦陈,该商标目前仍归工作室所有,“张家后人曾提出过共有,但是我们没有同意。”而法院此后也未追究商标注销一事。
“我们家族至今还是‘黑户’,没有‘泥人张’商标权。”张宇愤愤地说,他不得已又注册了“世家”商标,更强调作品个人属性,即作品价值主要取决于创作者。
“泥人张”的例子并非个案,随着“老字号”市场价值的再发掘,围绕其产生的权利归属争议也越来越多。
霍庆有是“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世家霍氏家族第六代传人。他发现一家画店擅自生产、销售标有“霍庆有版绘”字样的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后,将其诉至法院。最终经法院调解,被告保证不再销售原告产品,并当庭给付霍庆有3万元经济补偿款。
霍庆有认为,维护杨柳青年画版权是对老艺人的保护和鼓励,只有这样杨柳青年画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导演张艺谋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使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地戏的戏剧表演,但影片中却将其标为“云南面具戏”。安顺文化体育局认为,张艺谋和制片方侵犯了“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艺作品的署名权,于是起诉到法院,被法院驳回。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按照著作权法,署名权是作者对作品的权利。安顺地戏与京剧、评剧一样,仅是一个戏剧种类,本身不构成作品。只有安顺地戏中某一个特定剧目,才能构成作品。这一判决也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后继无人的传承尴尬
与非遗产权纠葛不同的是,更多的非遗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突出的问题就是后继无人。
今年57岁的陕北说书传承人韩英莲是国家级传承人。“我是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我父亲是盲艺人韩启祥。”她说,自己小时候不爱说书这门艺术,因为说书从古至今都是盲艺人吃饭的手艺,女说书人更是前所未有,从事说书总觉得被人瞧不起。但父亲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就要培养几个有文化的,特别是女弟子,自己的女儿自不待言。渐渐地,韩英莲逐渐喜欢上了说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最火时,她所在的班子会在一个村唱到凌晨,而第二天的演出早早就被另一个村预订下来了。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听的不多,学起来比较难,年轻人也吃不了这苦头。观众和徒弟都不好找。”韩英莲说,因为国家对非遗的重视,陕北说书的不少段子已经整理成文集和音乐,开设培训班也有专门场地。由于集市和农村红白喜事对说书仍有需求,说书剧团完全能够自负盈亏。不过即便如此,招徒弟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柳青年画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尽管杨柳青年画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但由于技法高超,作品别具一格,标有“霍庆有版绘”的彩绘年画,在天津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文化部也授予霍庆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只有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才能有根有魂。”回顾这些年磕磕绊绊的经历,霍庆有深有感触地说,政府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艺人们有意识的努力,使得杨柳青年画已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赢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杨柳青年画界唯一掌握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全套制作工艺的人,霍庆有对“接班人”的问题最放不下心。“儿子也能跟我学了,可找个徒弟却不容易。外边的世界诱惑太多,再加上这门手艺收入不高、比较单调,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前两天,一个学了八年的徒弟又离开了,只有六七个徒弟还在坚持。”
“广州有位导演到一个保留原生态的景区旅游时,看到过一项老技艺,等再回来准备拍时,唯一掌握这门技艺的老人已经去世了。少一个传承人就少一样手艺。”延安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尚鹏浩感慨道,非遗保护要有紧迫感,要跟老艺人“消失”赛跑,因为仅在去年,当地就有多位剪纸、腰鼓、民歌领域的国家级传承人去世。他同时认为,有些确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技艺,如农民地头下的游戏棋等,专门找人来传承并不现实。
非遗保护亟待政策支持
不久前,我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成功申遗让国人颇感自豪。然而,邻邦韩国将“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遗却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仅从非遗保护而言,我国并不缺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经拿出专项资金给予支持,但从现实看,仅仅是资金支持还远远不够。
采访中,张宇提出一个问题:“家族父子传承的方式是否有保留的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对我们的考验。但我们要做的是有家族特点的泥塑。”国家对于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支持无疑有利于这门非遗的普及和发扬光大,但却忽视了版权这一关键问题。在品牌注册上又缺少与家族传人的沟通和利益共享,最终导致了双方不断激化的矛盾。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伟凯认为,“泥人张”的命运是我国民间文化遗产在商业大潮冲击下演变的一个缩影。我国很多民间艺术尽管长期作为非遗出现,却缺少产品品牌,为日后的品牌归属埋下了隐患。随着民间手工艺、老字号等的品牌价值日渐凸显,知识产权纠纷可能会愈演愈烈。
“从‘泥人张’的例子看,非遗传承首先要尊重既有传承,尊重版权,尊重市场规律。”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授唐锡光表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不能脱离市场。有些非遗传承脉络明确,有生命力,政府不应以保护为借口过多地干预,应遵循市场规律。
唐锡光同时也表示,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调节,否则具有商品价值的产品争相被模仿和注册,容易走向商品属性超越艺术价值的歧途。他建议,当一门非遗表现出不适应市场,或者有序的传承关系出现变动、存在难以传承风险时,政府应以托底的面貌出现,给予抢救性保护,同时在后续版权归属上与原继承人协商,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取得。
对于多数传承脉络不明晰、集体共有产权的非遗来说,从法律层面维护非遗的版权就变得非常重要。“必须针对可能日益增多的产权纠纷明确法律适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何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玉烨等专家表示,当前非遗保护国家层面尽管有非遗法,但缺少对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细则。现有非遗保护法偏重于行政保护,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缺乏有效衔接。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受访专家认为,非遗权利除了署名权还有很多权利。应当综合考虑非遗的特殊性和著作权法、专利法中人身权的内容。特别是对于财产权部分,可以借鉴传统民法的理论,再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规定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而且,保护民间文艺难以适用著作权法,而要用特别的法律法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填补这一空白。
唐锡光认为,对于非遗产权人广泛的,可考虑成立协会或基金会组织代为行使所有权,收益按相应比例分配,可以照顾到更多权利人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非遗私权保护限制其进一步发展。
针对一些缺少实用性或当代传承性的传统技艺走向衰落,专家认为,应通过普查有针对性地了解其面临的困难,探索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对于确实难以为继的,应尽快开展抢救性发掘记录,留下尽可能多的影像、文字资料,妥善保管、展示。
拿杨柳青年画来说,霍庆有表示,尽管现代家庭可能不再需要杨柳青年画了,但通过不断推陈出新,有的“移植”到了折扇、手机链、剪纸等不同载体上,可以极大拓宽生存空间。
尚鹏浩告诉记者,延安针对说书项目把老艺人全部纳入非遗档案,唱段存档,明确了传承单位。随着技术进步,他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收集传统农耕工具到群众艺术馆。对于难以再推广的非遗项目保护而言,延安的做法值得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优秀典范。与前些年非遗保护的资金困境相比,在国家各个层面的重视和支持之下,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不差钱”。
但随着“老字号”品牌商品价值日益凸显,围绕品牌权利继承所引发的争端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市场并不看好的非遗项目更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专家认为,新时期的非遗传承保护必须跨越这两道坎,才能实现传承的健康有序。
产权背后的利益纠葛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在天津当地,一公一私两个“泥人张”之间却由于商标归属,有着长达20多年的争议。双方在传承理念上存在矛盾,经营上彼此竞争,这也成为“泥人张”传承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
今年36岁的张宇是“泥人张”第六代家族传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官司分散了他很大的精力,其中最让他揪心的是与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官司。
本刊记者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的二审判决书中了解到,1958年天津市政府在市文化局领导建议下,成立了由张明山后代参与的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培养了新一代家族传人及非张氏“泥人张”彩塑艺术传人。随着张家后人从工作室退休,工作室自行将“泥人张”申请注册商标,独立拥有,并与家族传人在市场上竞争。
法院最终判决,彩塑工作室和张明山后代中从事泥人张彩塑创作的均为“泥人张”无形资产共有人,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工作室已注册的“泥人张”商标和“天津泥人张彩塑”服务标记应自行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
在法院判决“泥人张”名称使用权归双方共有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泥人张”家族传人与彩塑工作室各立门户,互相竞争。工作室所持有的商标也未申请撤销。第四代家族传人张铭的后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水火不相容。
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主任傅长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其设立和培养学生的主要宗旨是挖掘和推广泥人张彩塑艺术。他也坦陈,该商标目前仍归工作室所有,“张家后人曾提出过共有,但是我们没有同意。”而法院此后也未追究商标注销一事。
“我们家族至今还是‘黑户’,没有‘泥人张’商标权。”张宇愤愤地说,他不得已又注册了“世家”商标,更强调作品个人属性,即作品价值主要取决于创作者。
“泥人张”的例子并非个案,随着“老字号”市场价值的再发掘,围绕其产生的权利归属争议也越来越多。
霍庆有是“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世家霍氏家族第六代传人。他发现一家画店擅自生产、销售标有“霍庆有版绘”字样的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后,将其诉至法院。最终经法院调解,被告保证不再销售原告产品,并当庭给付霍庆有3万元经济补偿款。
霍庆有认为,维护杨柳青年画版权是对老艺人的保护和鼓励,只有这样杨柳青年画才能不断推陈出新。
导演张艺谋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使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地戏的戏剧表演,但影片中却将其标为“云南面具戏”。安顺文化体育局认为,张艺谋和制片方侵犯了“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艺作品的署名权,于是起诉到法院,被法院驳回。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按照著作权法,署名权是作者对作品的权利。安顺地戏与京剧、评剧一样,仅是一个戏剧种类,本身不构成作品。只有安顺地戏中某一个特定剧目,才能构成作品。这一判决也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后继无人的传承尴尬
与非遗产权纠葛不同的是,更多的非遗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突出的问题就是后继无人。
今年57岁的陕北说书传承人韩英莲是国家级传承人。“我是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我父亲是盲艺人韩启祥。”她说,自己小时候不爱说书这门艺术,因为说书从古至今都是盲艺人吃饭的手艺,女说书人更是前所未有,从事说书总觉得被人瞧不起。但父亲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就要培养几个有文化的,特别是女弟子,自己的女儿自不待言。渐渐地,韩英莲逐渐喜欢上了说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最火时,她所在的班子会在一个村唱到凌晨,而第二天的演出早早就被另一个村预订下来了。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听的不多,学起来比较难,年轻人也吃不了这苦头。观众和徒弟都不好找。”韩英莲说,因为国家对非遗的重视,陕北说书的不少段子已经整理成文集和音乐,开设培训班也有专门场地。由于集市和农村红白喜事对说书仍有需求,说书剧团完全能够自负盈亏。不过即便如此,招徒弟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柳青年画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尽管杨柳青年画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但由于技法高超,作品别具一格,标有“霍庆有版绘”的彩绘年画,在天津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文化部也授予霍庆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只有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才能有根有魂。”回顾这些年磕磕绊绊的经历,霍庆有深有感触地说,政府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艺人们有意识的努力,使得杨柳青年画已成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赢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杨柳青年画界唯一掌握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全套制作工艺的人,霍庆有对“接班人”的问题最放不下心。“儿子也能跟我学了,可找个徒弟却不容易。外边的世界诱惑太多,再加上这门手艺收入不高、比较单调,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前两天,一个学了八年的徒弟又离开了,只有六七个徒弟还在坚持。”
“广州有位导演到一个保留原生态的景区旅游时,看到过一项老技艺,等再回来准备拍时,唯一掌握这门技艺的老人已经去世了。少一个传承人就少一样手艺。”延安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尚鹏浩感慨道,非遗保护要有紧迫感,要跟老艺人“消失”赛跑,因为仅在去年,当地就有多位剪纸、腰鼓、民歌领域的国家级传承人去世。他同时认为,有些确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技艺,如农民地头下的游戏棋等,专门找人来传承并不现实。
非遗保护亟待政策支持
不久前,我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成功申遗让国人颇感自豪。然而,邻邦韩国将“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遗却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仅从非遗保护而言,我国并不缺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经拿出专项资金给予支持,但从现实看,仅仅是资金支持还远远不够。
采访中,张宇提出一个问题:“家族父子传承的方式是否有保留的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对我们的考验。但我们要做的是有家族特点的泥塑。”国家对于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支持无疑有利于这门非遗的普及和发扬光大,但却忽视了版权这一关键问题。在品牌注册上又缺少与家族传人的沟通和利益共享,最终导致了双方不断激化的矛盾。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伟凯认为,“泥人张”的命运是我国民间文化遗产在商业大潮冲击下演变的一个缩影。我国很多民间艺术尽管长期作为非遗出现,却缺少产品品牌,为日后的品牌归属埋下了隐患。随着民间手工艺、老字号等的品牌价值日渐凸显,知识产权纠纷可能会愈演愈烈。
“从‘泥人张’的例子看,非遗传承首先要尊重既有传承,尊重版权,尊重市场规律。”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授唐锡光表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不能脱离市场。有些非遗传承脉络明确,有生命力,政府不应以保护为借口过多地干预,应遵循市场规律。
唐锡光同时也表示,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调节,否则具有商品价值的产品争相被模仿和注册,容易走向商品属性超越艺术价值的歧途。他建议,当一门非遗表现出不适应市场,或者有序的传承关系出现变动、存在难以传承风险时,政府应以托底的面貌出现,给予抢救性保护,同时在后续版权归属上与原继承人协商,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取得。
对于多数传承脉络不明晰、集体共有产权的非遗来说,从法律层面维护非遗的版权就变得非常重要。“必须针对可能日益增多的产权纠纷明确法律适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何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玉烨等专家表示,当前非遗保护国家层面尽管有非遗法,但缺少对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细则。现有非遗保护法偏重于行政保护,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缺乏有效衔接。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受访专家认为,非遗权利除了署名权还有很多权利。应当综合考虑非遗的特殊性和著作权法、专利法中人身权的内容。特别是对于财产权部分,可以借鉴传统民法的理论,再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规定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而且,保护民间文艺难以适用著作权法,而要用特别的法律法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填补这一空白。
唐锡光认为,对于非遗产权人广泛的,可考虑成立协会或基金会组织代为行使所有权,收益按相应比例分配,可以照顾到更多权利人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非遗私权保护限制其进一步发展。
针对一些缺少实用性或当代传承性的传统技艺走向衰落,专家认为,应通过普查有针对性地了解其面临的困难,探索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对于确实难以为继的,应尽快开展抢救性发掘记录,留下尽可能多的影像、文字资料,妥善保管、展示。
拿杨柳青年画来说,霍庆有表示,尽管现代家庭可能不再需要杨柳青年画了,但通过不断推陈出新,有的“移植”到了折扇、手机链、剪纸等不同载体上,可以极大拓宽生存空间。
尚鹏浩告诉记者,延安针对说书项目把老艺人全部纳入非遗档案,唱段存档,明确了传承单位。随着技术进步,他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收集传统农耕工具到群众艺术馆。对于难以再推广的非遗项目保护而言,延安的做法值得借鉴。